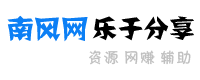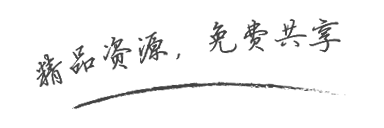文:从尚的视角看历史的专栏作家。
清代文学家李汝珍的小说《镜花缘》第二十三回“巴门咬字说酸,嚼字说迂”,说的是林志扬等三人到蜀国旅游,进了一家酒店喝酒。他们不仅遇到了一个满口脏话的调酒师,还遇到了另一个满口脏话的调酒师,一口气说了几十个“之”字。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这是文人学者之地,大家都不免附庸风雅,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笑话。
可见,附庸风雅本来就是一个贬义词,指的是用高雅文化装饰自己的庸俗之人,模仿别人有点不堪。附庸风雅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。明清时期,有的人不认识几个大字,却要用墨汁沾脸,用手指沾朱,表示刚写完字,是读书的种子;清末民初,西风东渐,有人在胸袋里插上两三支自来水笔,以示文明,很多只是笔帽。文革期间,样板戏大行其道,广为宣传。在北京和天津的街道上经常看到一些提着小提琴的行人。然而,如果琴盒被打开,真相就会大白。琴盒里什么都没有空,也不是个别现象。

附庸风雅的典型人物,张宗昌(没有肖坤),民国时期的军阀,可以算是一个。他没有读过一天书,几乎是个文盲。当他开始做土匪时,他投靠了奉系军阀张,并逐渐发了财。1925年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察。上任后,我觉得自己是个大老粗。如果我想在山东立足,我必须表现得像个君子和文人。于是,他邀请住在魏县的光绪癸卯科状元王寿彭做省教育厅厅长,并以他为师,请王寿彭教他读书写诗。
他也是附庸风雅,出版了一本书《肖坤·史超》来表达友谊。他的诗俗到让人忍俊不禁。比如王寿彭给他讲了楚汉之争,他听了之后,接连写了两首诗,其中一首是嘲笑刘邦的:
听说项羽拉了山,
吓得刘邦就要逃跑。
不是我的小张亮,
奶奶已经回沛县了。
二是模仿刘邦的《风歌》,做一首《我也写风歌》:
开炮射他妈!
威海内西回家!
数英雄,张宗昌!
一条巨鲸吞了扶桑!
张宗昌的家乡是山东高密,他也想像刘邦一样在家乡展示自己。在回老家的路上远远地看到泰山,激起了他的诗意:
看远处的泰山,
上细下粗。
把泰山颠倒过来,
头薄头厚。

不过,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附庸风雅一分为二。为做作,求虚荣,把“优雅”当面霜的“附庸”,应该是可鄙的;而“优雅”却被视为一种高标准,作为自己的审美追求,是中国人对优雅、高雅的希望。换个角度说,人为什么要附庸风雅?它反映了一种欲望,一种人们想要摆脱庸俗的处境。
当一个人试图附庸风雅的时候,说明他至少知道优雅是个好东西,他已经具备了对优雅的要求。这是他远离庸俗,走向高雅的良好开端。与其庸俗,不如附庸风雅。附庸风雅久了,不优雅就变得有些优雅;假高雅变成真高雅,比以低俗为荣,不屑高雅要好得多。谁能无师自通,自然优雅?
附庸风雅其实是人性,人性追求美好向上。优雅是艺术的象征,是美的代名词,让人不禁唯唯诺诺。只要世界上的愚蠢、可耻、下流、犯罪、邪恶和暴行存在一天,艺术就可以在阳光下正当地存在。附庸风雅即使不是最有益的善,至少也是最无害的恶...,它根本不是恶,而只是未成形的善,只是不完美的善。

一个附庸风雅的人,至少没有尽力作恶,至少没有肆无忌惮地践踏正义。仅附庸风雅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对美好和高贵充满了向往,并且在竭尽全力地勉强模仿。这也有什么不好,难道是去见圣贤斯琪?每个附庸风雅的人无疑都是善良的人。谁会忍心嘲笑或鄙视一个善良的附庸风雅?
其实文化上的一时低俗并不可怕。重要的是知道低俗,能够跟风求雅。没有所谓的天生高贵典雅,必然会有一个初级阶段的“附庸”求雅。有什么好笑的?